问现在处在一个迷茫的街头,除了开车,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怎么办。
什么都做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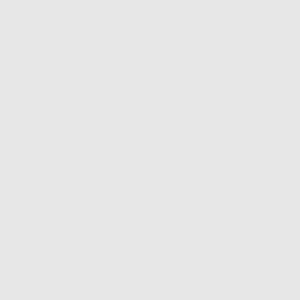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Vitamin
Vitamin
-
游戏王决斗链接卡组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存在的,每一种的效果都不太相同,有的会比较的厉害,有的就一般般了,在2021的新版本当中,选择合适的,才能够发挥出最强大的效果来,具体来说的话,有哪些是比较好用,什么样的更加厉害呢?下面来了解一下! 游戏王决斗链接卡组推荐 传奇卡组推荐 卡组搭配 因为试削**组我已经卡在传奇2三天了,反复升降,现在研究出来的这套胜率已经可以上分了,现在又回到传奇2了。 先说一下卡组思路: 角色是利希德,技能第一个就能解锁,发动陷阱打200,补伤害。 核心是白兵战,炎战士,燃烧大地(只要1张)和碰瓷剑,这三张是主要伤害来源,除了烧地全部满上。 佯动作战和异度生物,至少2,最好3;飓风和阿努比斯的诅咒(现在我还没有诅咒)都是有就带的;仓鼠可以用**龙代替; 其他打法: 强欲壶,2-3张都可以,过牌还能打200,非常好用,我这里只带2,因为卡太多了。 金苹果,可以带点其他的,比如保安球,这张是可以替换的。 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女神的庇护(回3000),守墓官(召唤打500),都可以考虑带。 后手起手记得防心镇壶。 主要打法就是狗场,拖到伤害牌到手,这里说一下记得在设置里开自我连锁,切记。 本套卡组所有的卡都可以白嫖,除了(人马跟,苏醒之魂)要抽卡,但是重点,不用花钱,可以白嫖! 用宝石抽奖,抽奖保底60包,我是30包出的不算非也不算欧,就算是酋长抽光卡池也才3000宝石,前面送的宝石加一起就有3000了,再做完一些任务,只要不乱花,存个8000宝石没什么问题,够接下来的一系列花销! 卡组解析 角色用城之内克也,带天赋,战士的领域,因为战士族攻击偏高,加上城之内克也的天赋前期就让你处于优势,大c,青眼白龙带三张是关键 战斗思路,骑士技能第一张优先选卡组里面的送去墓地或装备(不要选手牌里的)青眼白龙装备避免卡手,第二次选弧光烈焰龙,巧诈师有可以选弧光烈焰龙献祭,触发墓地重生提前是你墓地里面有一条白龙! 其他的(灵魂交换跟苏醒之魂,触发特殊召唤白龙我就不说了你玩几局就明白了)你玩几局就大概能懂这**的强度,20张牌,15张怪兽,5张魔法陷阱,好招白龙不卡手,遇上氪金卡组都不虚,决斗世界无压力打40级人机刷卡,唯一的缺点城之内召唤青眼白龙没有中二的台词动画 天**有也没关系,给死者的供奉也可以不上,只要在对面纳寂魔出来前,不要召唤除巨龙骑士外的其他怪兽就好了,对面纳寂寞出来一看,是一只骑着巨龙的骑士,就直接守备表示了 虽然也可以刷分,但是感觉用城之内的战士领域更好点(卡组不变),因为对面1900攻的双子精灵不好解,战士领域给巨龙骑士+200攻刚好可以解。 贫民卡组,魔力去除两张,混沌魔术师(不受怪兽效果影响,商店可以买,6星怪)是关键,配合装备卡黑色项链,其他展开自己配。我是杂牌卡组,一般打四十级7 3开,魔力去除破坏卡通世界是关键。我是这么打的,用上收益结晶,要么红色结晶,我反正奖励都拿到了。
-
问 档案在自己手里一年多了,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11 05:39:32
答 1、拿着你的档案去所在城市的人才市场,然后放在人才市场托管,每年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2、找一份工作,一般公司会要求调档,这样就是公司帮你代管档案了。不过在**,...
-
问 90后的我感觉好迷茫,你们迷茫不?
提问时间:2024-05-11 15:24:46
答 谢谢悟空小秘书邀请。刘同写了一本书,名字叫《谁的青春不迷茫》,我想这本书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我也曾经迷茫过,甚至现在依然迷茫,如果要问如何走出迷茫的情绪,那么我会...
-
问 对现在的工作感到迷茫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11 11:46:54
答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深有感触。对于工作很多时候都会感到迷茫。看到你的问题描述,我想还是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工作了了一年了,工资没有上涨,依然是2600元,...
-
问 不知为什么总感觉有股火在自己身体里燃烧,怒气充满了自己?
提问时间:2024-05-11 17:31:50
答 呵,我是搞中医科的医生,从你表述来看,我估计你是肝火旺,肝经有郁热,气机不畅的原因,建议去医院看看,吃点中药。效果很好 呵,这类病人现在每天都很多,和现在的生活...
-
问 我感觉自己的感情好像被诅咒了。 如果感觉自己被诅咒了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11 10:03:45
答 感觉自己好像被诅咒了?那有没有什么很显性的征兆啊?因为被诅咒的人都是有征兆的啊,如果觉得自己的生活跟之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我确定你就是在疑神疑鬼,如果确定已经...
-
问 没做上自己喜欢的职业,迷茫中,我该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11 21:12:52
答 你喜欢啥职业?如果你喜欢、够执着,你可以努力自我学习,我想你所喜欢的职业未必在你当地只有1家这样的公司吧,机会肯定是有的,别放弃,你可以的
-
问 分手三个月,感觉自己快崩溃了,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11 11:15:11
答 分手,原因是什么?其实,无论是什么现在都不重要了。既然分手,对方一定有分手的理由。因为,是你痛苦。说明提出分手的人一定是对方。当她对你失去了感情。你是否感觉还有...
-
问 为什么感觉自己做什么都像在学习,并且还是以旁观者的心态去看自己.....
提问时间:2024-05-11 18:15:03
答 你好因为内向,所以每件事情都想得比大众通彻!而当有一天,碰到一件事情是曾经自己看的很透彻的时候,就会有种自己在旁观这个世界的感觉!说准确的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往...
-
问 我现在快毕业了,感觉学煤炭深加工与利用这个专业,感觉到很迷茫
提问时间:2024-05-11 02:46:04
答 现在无论是专科还是本科,毕业之后真的是大部分都不是专业对口的,你现在就可以慢慢寻找和你专业对口的工作,或者相关专业的工作。实在找不到如意的,你就考察下现行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