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涯明月刀镇派武器为什么加特效
《天涯明月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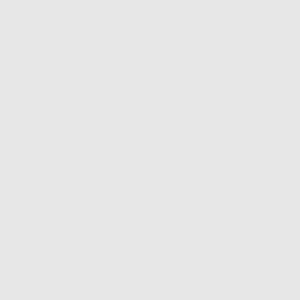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Lindsey36
Lindsey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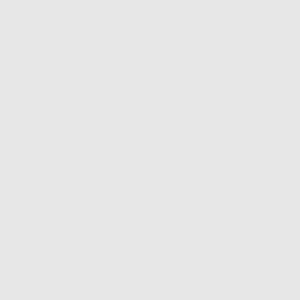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芥末
芥末
南行记(艾芜)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幺厮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幺厮呼喝一声:“喂!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幺厮的脸,又移射着我。“你们俩一床睡!幺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没有吃饭,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个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拼命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捱饿!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用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采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托词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草鞋塞在裤裆里,满神气地、又像作贼一般逡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到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出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的棒了。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你要买几双?作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嘿,再添一点钱,就够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去你的!不要了。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锣,我掉身就跑。“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双来!“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我走进一家烧饼店,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一面问着价钱。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一个铜板一个!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铛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个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计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铜板!“嗯,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是当十的铜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诧异地问。“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伙计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对于现存的财产,就没有刚才那么乐观了。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头一个饼,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第二个,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还渴想要,觉得有点不对。像悭吝老头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竟也有了。终于忍不住,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还没有饱。不过,人是恢复元气了。有了元气的我,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领略异地的新鲜,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舐舐嘴角上的烧饼屑。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瞠啷瞠啷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在各街闲游,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夜深回去。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同时一支烟,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我望见他递给烟支的手颈,密散着黑顶的红点,登时使我怕起来了。“呵呀,今晚要同一个生疳疮的人睡,怎了得!这由心里弹出的声音,幸好忍在唇边了,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支退了。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我周身的皮子,也急地发着痒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干脆的拒绝。同我睡的伙伴,是终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足板…
我憎恶着,恐惧着,昏昏迷迷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也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足杆,只要拉起裤脚给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足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娓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么?“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足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乐。“你认识街道么?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认识的。“真的么?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么?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丝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我。“这是一定的...
-
问 天涯明月刀ol什么门派适合打每天的战场
提问时间:2024-04-28 20:33:20
答 每日的战场,最适合的是唐门、天香等远程职业;其次是真武神威,一个半远程带离渊控制,一个皮厚有霸体与位移;最后就是打酱油的太白丐帮五毒一类了。
-
问 天涯明月刀ol珑铸多少个能出特效
提问时间:2024-04-28 09:48:22
答 无友传奇夺宝奇兵可以说一个拼实力的活动,拿宝箱的人一定要强力而且队友还要多大家保护好,得到宝箱的人就会有随机奖励。
-
问 天涯明月刀天香的加血技能为什么不能用
提问时间:2024-04-28 13:47:25
答 首先需要切换到治疗状态 然后打开p 拉出你治疗状态所有能用的技能包括绝命伞 唯一的输出技能 以及解控技、回香技能、消除duff技能 还有4个加血技能 1个风墙 ...
-
问 天涯明月刀神刀门派在哪打坐
提问时间:2024-04-28 15:51:39
答 徐海左上角,传送到归刀殿,然后跳下台子就是了。其实去哪打坐都行的,不一定要回本门派的打坐点打坐。另外告诉你,点雕像有惊喜。
-
问 天涯明月刀燕云91话本掉什么武器或首饰
提问时间:2024-04-28 21:21:29
答 应该在那个攻略方法里有介绍的,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去看看现在最具期待的手游,也很不错的。游戏最好下网易版本的,非版本会出错误。邀请码gsaz6230gsas716...
-
问 天涯明月刀帮派建筑怎么建造和任务在哪接 天涯明月刀帮派攻略
提问时间:2024-04-28 12:42:48
答 随机出现在河南省嵩山南部的无极洞深处(杀刀客会随机出现);击败后随机掉落+1~+4修练加给值的防具;掉落物品:软剑,戒刀,青钢铁戟,飞鹰爪,绸缎衣(上、下),水...
-
问 天涯明月刀 帮派建筑 为什么不给建筑经验了?
提问时间:2024-04-28 14:21:07
答 鉴于当前官方对帮派系统做了少量微调,现在帮会建设会比之前稍微简单一些。帮会升级的全攻略,想要让自己的帮会变得更大更强的同学不妨一看。这次帮派玩法攻略主要讲一下几...
-
问 镇魂曲和天涯明月刀 哪个好玩
提问时间:2024-04-28 20:40:14
答 综合来说,镇魔曲比较好玩。镇魔曲以藏地的文化为底,包括建筑等方面也是特地去考察之后设计出来的,画面很有藏地以及古时的风貌;而且运行流畅,人物比较容易控制。而且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