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古墓丽影崛起dlc芭芭雅嘎女巫神庙寻找解药怎么通关
古墓丽影 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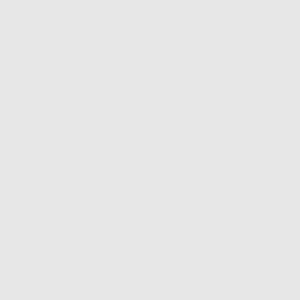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supergirl
supergir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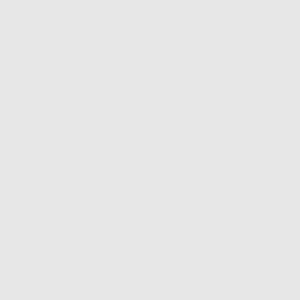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晨里的月光
晨里的月光
金庸小说叙事结构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小说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图式、一种骨架,相当于建筑中的立柱横梁,使整部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话。一个结构往往包含着若干可以解读却又难以一时解读甚至长期解读不尽的文化和审美的密码。金庸小说所展示的意义世界,藏着一些思想结构,文章运用叙事学原理,将金庸作品中最基本而又共通的意义一一还原出来,按其小说组合要索的变化列成模式,多层次分析了金庸小说的三维结构形态。金庸继承并改造传统叙事模式,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透过纷纭复杂的情节,贯穿其中的是金庸小说的三个母题:寻找自己—爱的困惑—归隐情结,形成一种主导性模式—“生存模式”,作者有意识地揭示人类的生存处境,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金庸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具有多重内涵的悲剧描写: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环境要素以渲染悲剧气氛,让人物从命运、爱情、性格、人性诸方面去演绎悲剧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独特性情节设计形成双重悲剧;“假喜剧”的悲剧形式的选择…这些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对悲剧本身的突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反武侠”发展过程,反映为他对包括武侠人物身份和武侠小说主题的认识的渐变,是从传统文化之侠到无侠、非侠的对侠的否定,“反武侠”的实质,既包含他对自我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武侠”的结果,是“后金庸”武侠小说的衰落。从武侠小说文类的内部因素包括时代背景、人文信仰、人性因素、象征色彩等方面进行变革提高,从外部因素包括武侠文类的杂合性与边缘性、对武侠小说作者的要求入手,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仍然是有前途的。金庸小说的特点:一是丰富性,多种多样,包括了古今中外各种小说回目的形式;二是创新性,用诗、词做标题,这在古今小说回目中少见。金庸创作经由对于主体性的怀疑而获致宽容多元价值的后现代性立场;由此,儒、道、佛及现代性文化价值并存于虚构的江湖世界,在对峙、交谈、相互解构中明晰地敞亮各自的意义和局限;进而,尊重边缘话语的存在意义破除了对于一切中心价值强制性统治的**,肯定了人类生活摆脱异己价值看管的狂欢状态的内在诗性。以虚构写真实
《射雕英雄传》中,即便金庸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但从本质上来说,小说依然是文学虚构的产物,无法巨细靡遗地刻画出当时历史的每一处角落。首先看“郭靖”这一人物。历史上确有此人。据《宋史·忠义传四·郭靖》记载: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厓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金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这件事发生在1207年,而《射雕英雄传》中写的就是自1196年始到1221年结束,从这一点看,时间上是符合的。只是这个侠义人物死得太早,在他死后十几年,成吉思汗才率军西征。因此,历史上真实的郭靖并不像金庸笔下的郭靖那样风光八面,在蒙古大军西征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更是子虚乌有,此“郭靖”非彼“郭靖”。但可以确认的是,《宋史》中这位“郭靖”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射雕英雄传》中老实木讷却勇猛担当的“郭靖”形象倒是如出一辙。显然,“郭靖”这一人物本身具有部分历史意义的真实,同时也具有金庸主观创作后的虚构性。另有一例,在小说的最后,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人在草原上驰骋: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郭靖吓了一跳,才知自己把话说重了,忙伸手扶住,说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语多有冒犯,请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张脸全成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急驰而回。当晚成吉思汗驾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在《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当晚就驾崩了,与书中时间点对应,在1221年。而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成吉思汗驾崩是在1227年,金庸让他早死了6年。能确定的是文学创作正是在文学与历史的这种虚实交错的盘根错杂中而产生。假若小说中成吉思汗与郭靖对话之后并无任何举动,这一段对话充其量也就是小说中为情节服务而存在的许多虚拟对话之一。但金庸故意借郭靖之口,批判成吉思汗杀戮好战,并虚拟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成吉思汗本身重病,听了郭靖之言,茫然若失,病急攻心,当晚驾崩。这就使得郭靖的这一番言论格外惹人重视,尤为凸显犀利与分量之重。在金庸看来,**与杀戮不该是英雄之举,而只有在郭靖口中,“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寄托着他心中的英雄主义。显然,虚构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目的也在此,金庸在塑造着他内心认可的英雄。身体叙述策略
金庸小说最常用的“身体叙事”策略是以“弱”写“强”,该叙事方式颠覆了人们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增加了不可预测性,解放了侠客的身体,让高强的武功不再仅仅寄身于“相貌堂堂”的躯体之中,各种身体形象都和武功产生了紧密联系,使读者与侠客身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武功的高低与身体的“高大强壮”没有必然联系,相反,那些“肌肉猛男”往往是武功较低甚至不堪一击的。武功真正高强的侠客往往瘦小斯文,甚至老弱病残,他们以“柔弱胜刚强”的深刻反差。金庸小说中侠客身体“弱”的表现有四种:
第一是矮小瘦弱的身体。这似乎与高超武功无缘,但在金庸那里却偏偏武功高强,这种打破读者惯常思维的“陌生化”策略,在金庸小说中十分常见。金庸大量使用了这一叙事策略,说明这是一种自觉的叙事机制。这种叙事策略断绝了身体与武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让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构了日常定式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侠客的印象,使侠客世界增添了一份神秘。第二是残疾缺废的身体。成为大侠并不一定需要身体素质的“天生异禀”,残疾缺废同样可以成为武林高手。这也是金庸处理侠客身体的一个叙述策略,同样是以强烈反差来丰富侠客的身体。残疾缺废的武林高手很多,如洪七公、梅超风等。侠客们残而不废,残疾人同样可以独霸一方,练成独门武功。第三是疾病缠身的身体。一些武功高强的侠客却总是病怏怏的,都总是“一副病象”。武林高手却“满脸病容”,让人们对身体与武功之间的诡谲关系不敢轻易下判断。病怏怏的身体与惊世骇俗的武功结合在一起,出乎意料地消解了读者的习惯思维,增添了侠客武功的神秘莫测感和身体的吸引力。侠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使得侠客叙事亲切化、日常化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叙述”。日常可见的“平常身体”与“不平常”武功之间的关系,让读者在熟悉中品味陌生,感觉伸手可触却又遥不可及。英雄凡人化、凡人英雄化是《射雕英雄传》的一种美学效果。第四是与“武”相对的“文”。金庸笔下有很多“书生”侠客,书生的惯常形象是斯斯文文的,与侠客相去甚远,但在金庸笔下偏偏是侠客,外表清雅而武功高强,让人不敢小视。《射雕英雄传》“江南七怪”之一朱聪,是书生型侠客。书生的文雅外表与强悍功夫形成鲜明对比,让侠客的身体又一次变得让人震撼,身体的层次更丰富曲折,“文”与“武”以身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好处是引起读者的惊叹之情,以反差使读者不由得“停顿”一下,调动读者积极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武功对身体的“背叛”所产生的张力,大大激活了对侠客世界的超越性想象,身体不再是武功的直接表意符号而有了“文学功能”,成了对压抑的反抗与自由的叙述。这些“反常”的叙述,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解构惯常的简单对应,建构新的复杂关系,既是对武侠神秘性的解构,又因身体与武功之间的不对称建构了新的神秘。当然,身体本身的高大威猛自然是侠客的先天优势,更容易在江湖立足。俗话说“一力降十会”,强壮身体与高超武功的“强强联合”自然更有大侠风范。虽然身体本身的先天条件并非成为侠客的前提,但金庸也不会刻意回避、抛弃高大威猛在侠客身体中的地位,如果那样反倒不真实了。金庸笔下高大威猛型的侠客也相当多,这使侠客的身体叙述显得更自然真实。《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药师、欧阳锋都是魁梧异常。高大魁伟型是金庸众多侠客正常身体形态的一种,是一种正面叙事,是一种明写、实写,相当于“破”中之“立”、“逆”中之“顺”,顺应了读者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有正有反,有破有立,叙事层次因而更丰富。“美”的身体
侠客身体叙事中的最耀眼之处是大量的女侠,女侠在江湖的行走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变得万紫千红,改变了侠客身体世界的结构。从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而言,女性侠客的出现,整个影响到江湖结构上的体质改变,主要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这不但使得江湖的阳刚气息得以藉柔情调剂,更连带影响及英雄侠客的形貌与性格的描绘。大量女性美丽迷人的身体,改变了侠客世界男性主宰的身体结构,减缓了紧张的气氛,多了一层浪漫色彩。女性在金庸小说中是真正独立的侠客,而不是装饰的“花瓶”,不是武侠世界的“她者”,不是单纯用来“养眼”的美女,也不是用来吊人胃口的陪衬。一些女侠甚至比众多男侠还要有魅力,她们不再是边缘而是中心。金庸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女侠客柔美身体里的无限能量,叙事重心向女性倾斜,众女侠在武侠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金庸对武侠小说叙事转变的巨大贡献。既然是美女型侠客,自然有万种风情。柔美的身体之中蕴含着高强的武功、善良的心灵与智慧,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多了一种圣洁的美丽,成为武侠世界最美的风景。把美女与武侠结合得如此生动自然,给读者无限的想象、愉悦与美感,这是金庸小说最成功的魅力所在。自金庸小说的女侠叙事开其端倪,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欲望客体成为叙事主体,女性第一次真正成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对女性的一次武侠大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不能否认,金庸小说中总是“梦中情人”一样的美丽女侠,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眼光中对女性的另一种“想象”叙述,也有一定的“美化”因素。“善恶”的身体
金庸小说侠客身体叙述的另一个策略是斩断了身体与善恶之间的单一定向关联,使善恶和身体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而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简单的好人好貌的“道德身体”。金庸在侠客的身体叙述中避免了简单的善恶对应与叙事者直接的道德“评述”,没有直接充当“审判官”的角色,这使得叙事视角更隐蔽,叙事更自由,人物形象可塑性更强。而且,这种叙事让读者产生的感情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感,而是混合的复杂情感。这种手法在金庸那里用得很多很纯熟。在金庸对侠客的身体叙述中,当然也有恶人与恶相的对应。恶人恶相的对应在金庸那里不是主要的,大量恶人长得非常美丽,善恶美丑之间产生强烈反差,给读者极大的冲击。男的儒雅,女的娇美,善恶与身体形象之间形成了多重的错综复杂关系,去除了符号化的模式,身体信息具备了多重隐喻性,读者有了更多回旋想象的余地,因而更有审美价值。更进一步就文化**而言,在某些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由于社会公正的缺失,**就和一些亚文化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限度和有条件的“私力救济”方式,并因此而被美化”,金庸小说的身体叙述手法,将善恶反转与侠文化的善恶反转形成同构对应,就避免了全知全能的**判断,在叙事**边界的模糊中获得了更好的叙事与审美效果。斩断身体和善恶之间必然联系的叙事还有一种:侠客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皆知,但身体却没有什么交代,留下无限“空白”与想象空
-
问 古墓丽影崛起这个地方怎么去
提问时间:2024-05-04 11:07:37
答 左边不是有个营地吗,过去后有个门,别进返着走,沿着水坑那走到头那有个梯子(剧情完成后出现)就能回到剧情中战斗的地方了
-
问 谁有《古墓丽影:崛起》所有的古墓攻略吗?
提问时间:2024-05-04 12:43:07
答 你可以去三大妈或游民搜索图文攻略,应该会有收获…不过总体上古墓的难度不算高,其实自己探索更有乐趣,实在搞不定再确认一下思路是否正确
-
问 古墓丽影崛起芭芭雅嘎支线任务卡bug了怎么办
提问时间:2024-05-04 04:43:44
答 **设施通讯失灵任务奖励:**工具游戏中遇到的第一个支线任务,需要破坏5个圣三一的通讯设施。支线任务的目标在地图上会以绿色原点显示,还是比较好找的。实在找不到的...
-
问 古墓丽影崛起冰冻之城古墓挑战怎么过
提问时间:2024-05-04 14:27:06
答 由古栈道的横梁跳到前面的冰壁爬上去,穿过冰墙,跳到船首的木杆上,走过去。右侧的墙壁上有可攀爬的地方,不过得先砸开上面的浮冰。首先扳动如图的机关,右边的绳索落下一...
-
问 古墓丽影崛起 挑战古墓都打了怎么过
提问时间:2024-05-04 06:00:14
答 失落之城挑战一-大肆破坏摧毁8个无头雕像,雕像耐久很高能吃不少**,推荐通过**枪和各类**物破坏。根据地图标记和图片你能比较轻松地找到7个,第8个雕像在前往基...
-
问 古墓丽影崛起dlc芭雅嘎女巫之庙求助
提问时间:2024-05-04 17:15:45
答 动作冒险大作《古墓丽影:崛起》首个剧情dlc—“芭芭雅嘎女巫之庙”已正式在xbox主机发行。该dlc提供了三个小时的额外剧情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新故事将带...
-
问 古墓丽影10崛起 买了本体通关过后 再买dlc 怎么显示无dlc
提问时间:2024-05-04 13:24:51
答 楼主,你好!有的啊,在steam库的游戏的dlc菜单里显示已安装,前提是你确定购买成功了
-
问 《古墓丽影》崛起熊怎么杀 ?
提问时间:2024-05-04 00:50:51
答 一、杀熊我们要利用到毒箭,毒箭的制作配方如下。二、第一个素材是普通弓箭,第二个素材击杀敌人可以搜刮得到,第三个毒蘑菇,在山洞入口即可采集,按下手柄右摇杆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