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金银锁的修理装备是系统自动修理还是**自己修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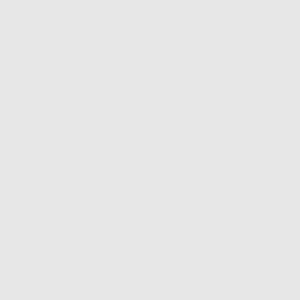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要萤邮痈阅帘柳
要萤邮痈阅帘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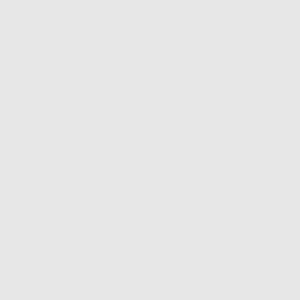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戒赌日记
戒赌日记
展开全部[内容提要]汉末建安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之疾疫盛行,文士们处境艰难,命运难以自保,一种末世之悲笼罩在人们心头。动荡的现实、悲情的审美作用对人们忧患意识的唤起,决定了此时文学情感的抒发以悲为主。建安文学以慷慨悲凉为主体特征,以情感抒发为主旋律,是念乱忧生的悲愤和伤感。悲凉、悲愤、悲哀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情感抒发的主要特色。本文运用有关的西方美学理论来对建安风骨进行分析,试图阐释建安风骨的内在美学本质。[关键词]建安风骨;美学阐释
一
建安文学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指出的:“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实质上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激动,建安文士们“酣歌”“慷慨”的潇洒行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内心深处的生存危机意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种历尽沧桑的“速老”心态。因此,建安文学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慷慨悲凉之气。(一)、建安文士的生存困境
汉末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自黄巾**之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相互混战,加之疾疫盛行,以致生民涂炭。“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除此之外,瘟疫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阎门而痘,或覆族而丧。连绵不绝的战乱和瘟疫共同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可以说战争和疾疫是剥夺人类生存权利的两大罪魁祸首。面对“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这样一幅幅凄惨的社会图景,文士们的感官何以不受到强烈的刺激?他们的灵魂何以不受到苦难的折磨?于是,一种“人生苦短”的生存之叹油然而生。人生短促,即使是正常颐享天年,然与悠悠历史相比亦如掠过天际的流星,转瞬即逝,更何况汉末文士又处在硝烟弥漫的多事之秋呢。敏感的文士们对此是有深切领悟的,曹操就曾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曹植《瀣露行》);徐干亦云“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徐干《室思诗》)。人作为具体的生命存在物,有生就有死,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然而汉末的战乱、瘟疫、灾荒却又在无情地吞噬着人的生命,生命在死亡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它的存在如同“朝露”、“暮春草”一样短暂。因此,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忧虑是时刻萦绕在文士们审美视界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二)建安文士的精神迷惘
如果说建安文士的性命之忧还仅仅是表层困惑的话,那么精神上的价值失去归所则是建安文士们的又一困境。由于一些强力人物纷纷而起挑战帝权而造成的战乱和政权频繁更迭,“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遭受严重破坏,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开始瓦解。加之老庄哲学的传播,士人群体逐步将关注的目光从外在的社会责任,转移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关注自我,重视个性,在以关怀民瘼,建功立业为主潮的建安时期,越来越为士人们所接受。这一特征更重要的是功业下面的内在精神和人的自我价值。即:个人价值及其实现是以功业追求为表征的。这也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人的精神面貌:世俗的神灵、皇权在强力(权)面前日渐式微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人,他们一方面与强力人物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抗争中,他们认识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以及这种抗争本身的无意义。于是他们希冀从真实存在的自我中找到这个完整的、内在的、自由的“我”。这种愿望作为个体性而普遍存在于文士们的心中。在两汉儒学中,天人一体是宇宙至美至善的系统:天道任德不任刑,天意重生不重杀,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汉末长时期的大规模战乱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无疑在现实层面上消解着两汉儒学的根基。既然人可以与天地并存,为什么性命如风中之残烛,转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既然天道重生不重杀,为什么众多黎元都死于非命?这一系列发自内心深处的诘问,不仅反映了人们从对生命个体本身的忧虑,而且还扩展到对生命个体之外的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忧虑。“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曹植《箜篌引》)诗人在极乐之时,**的神经突然清醒,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知命复何忧”所告诉我们的决不是诗人知命无忧,消解了心中的沉郁与悲凉,而是无能为力的**。再如曹操《短歌行》所言:“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忧思不绝如缕,所忧的是什么呢?魏武虽未未言明,但是那种难以言传的深层忧患—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忧虑—这样一种模糊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二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个性化创造活动和结果,它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要体现创作主体的情感、思想、意志和愿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创作主体的生存境遇必然会影响其审美判断,从而影响其创作风格。“现实的社会生活绝不是艺术家的敌人,它造成痛苦和失望,但对于艺术激情的产生来说,这恰恰是必要的准备。[1](p194)正如刘勰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因此,建安风骨所透露出的悲凉慷慨之气使人触目惊心,其忧郁悲凉之感让人心绪颤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刘勰的这段话可谓是对建安文士创作情感的最好描述。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惘,这双重困境必然会在建安文士们的审美情感上留下深刻的痕迹。袁济喜先生在其著作《六朝美学》中指出,建安文士们所崇尚的“梗概多气”、激昂慷慨无疑是一种属于“崇高”范畴的美。他认为:“所谓崇高,从审美心理学来说,就是由于对象空间的无限,力量的狂暴,冲破主体审美对象时想象和知觉的和谐运动,引起恐惧、悲哀等心理阻塞现象,最后唤起人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由于主体具备的理性和道德感能够承受和抗拒对象的威力,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先惧后喜的愉悦感,即崇高的审美情感,它是一种不和谐的美。[2](p52)审美肇源于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不同表现,就会使审美主体相应地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从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审美判断和评价。崇高作为反映人生命价值、意义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一,与审美主体自身因素(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等)以及在审美过程中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由于频繁的战乱和疾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大批建安文士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曹丕《与吴质书》)如果说生命在瞬间的消逝只是一种命运的劫数,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话,那么精神价值的失衡和无所归依就更促使文士们对人的生存价值意义进行思考。一方面正是人们面对战争的摧毁强力,感觉生命的存在力量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另一方面社会价值的整体失衡,可以说又毫不留情地给了人们本已脆弱的灵魂以沉重一击,似乎他们所做出的种种抗争、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渺小。“崇高体验大都是艺术家遭受心理挫折时的异常体验。在自然界的外物面前,不管是数学的还是力学的巨大或宏伟,都首先给艺术家以威慑和震撼,迫使他自惭形秽,反躬自问:在如此苍茫的宇宙中,作为如此渺小的生物,我的存在是否太可贵是否太可悲、太可笑、太脆弱、不值一提?[3](p142)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安时期的战乱、疾疫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失衡可以说是崇高感产生的契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指出:“(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4](p83)“在审美评判中,克服障碍的优势只是按照抵抗的大小来评判的。但现在我们努力去抵抗的东西是一种灾难,如果我们感到我们的能力经受不住这一灾难,它就是一个恐怖的对象。所以对于审美判断力来说,自然界只有当它被看作是恐怖的对象时,才被认为是强力,因而是力学上的崇高。[5](p99)对于康德所说的“瞬间阻碍”,朱光潜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这不是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某个个人觉得危险迫近时那种恐惧,而是在对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式在操纵着人类的命运。[6](p89)康德的这段话为我们阐明了崇高产生的心理机制。借助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追溯建安文士在当时客观社会环境下的独特的心理历程。如上文所述,战乱、疾疫所导致的人的生命存在犹如草芥一般不值一文,社会**道德的整体失衡、精神家园的无所寄托又将他们推入了迷惘、忧虑和失落的万丈深渊。这种生存浩劫与信仰危机,对建安文士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具有“拯世济民”优良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又是激发他们“在痛苦中将对人类命运的沉思负载在自己肩上,以寻求人类幸福的曙光和达到目标的突破点”[7](p144)的最好动力。“艺术家的崇高体验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可以借助于各种表现手段,把其内在复杂的感受和激情体验物化为可以供俗世各种人感知和玩味的形式,别人亦可借此以窥知人类崇高体验的生活。[8](p144)朗吉**斯也在《论崇高》中指出崇高的五个源泉: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严谨的结构。并且他还认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9](p126)崇高风格是伟大思想在语言上的反映。什么是伟大的人格呢?朗吉**斯的答案是:“胸襟旷达、志气远大”,也就是说,须有旷达的感情和远大的思想。在他看来,胸襟旷达,志气高远,内心对真理充满渴望,才能使思想变得崇高。至此,建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感就不难理解了:明净的大自然与错综复杂、肮脏丑恶的社会人事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文士们极易领悟山川草木之不朽和个体生命之卑微,便不由自主地升腾起崇高的愿望,从而努力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无限的宇宙天地之中。在对物质不灭而人生短促的崇高(审美)体验中,一股浩然正气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作家的心灵,激发他们的人格力量和向上的决心去与巨大狰狞的外物抗衡,以超越挫折,最终实现“我”(人格力量)的升华,使“我”获得非凡的能力和意料不到的观世高度。三
“审美是超越有限的最佳方式和摆脱悲剧性困境的唯一出路。[10](p102)审美何以能使人超越有限呢?这是由于美乃是在有限中“终于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谢林语),“是永恒事物的启现”,“是瞬间的持续(永存)”(乌纳穆诺语),加之人对无限、永恒有着极其强烈的本能渴望,因此人在审美过程中便很容易投身于这位在有限中漫游的无限女神的怀抱中去,从而臻于永恒圣洁的人间天堂,这便满足了人超越有限的本质欲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说:“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的峰巅。[11](p9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柏拉图、庄子到康德、席勒、谢林以及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宗白华等无数先哲都对审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殷切的期望,并赋予审美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重任。正是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疫、灾荒和**纷争,建安文士们才从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意识到人生的短暂与无常,进而探索一种超越有限生命的永恒价值。换言之,正是由于死亡所规定的人生有限性逼迫人们去寻找一种东西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迫使人去参悟死,去从必死中追求永生,从短暂的有限生命中创造出永存的终极价值。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像在非常严肃场合的一场游戏,在所有生命都必将终结的阴影下,它顽强地生长,渴望着超越。[12](p44)个体的生命存在如果单从物理(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它与整个人类历史相比简直就是“渺沧海之一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如果个体生命能够不断追求那“不可企及”的无限、永恒,踏上超越有限的悲壮征程,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有限而达到不朽与永恒,他的有限生命就可能获得永恒的意义。因此,当死亡、痛苦、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建安文士们没有沉沦,而是昂起高贵的头颅!他们没有在灾难面前消极避世,以求得个体生命苟延残喘,
-
问 dnf买了自动修理怎么不能修理武器
提问时间:2024-05-07 09:45:50
答 进入地下城即可自动修理。自动修理是检测你武器/装备耐久为0的时候自动修理,并且在地下城中有效,进入地下城即可自动修理。随便进一个图打一下就自动修理了。《地下城与...
-
问 dnf为什么我的自动修理不起作用
提问时间:2024-05-07 05:48:35
答 自动修理是检测你武器/装备耐久为0的时候自动修理的而且是在地下城中有效你武器已经为0再买不要紧的,但是你需要进入地下城随便进一个图打一下就自动修理了个人觉得,除...
-
问 哪个契约能自动修理装备着
提问时间:2024-05-07 06:11:31
答 自动修理当你所有的装备栏里 一旦有一个0耐久度的武器或者防具 它就会自动修理所有的装备 每天可以这样修理6次 我刷一管疲劳都够用的但是有个缺陷 当你在这个图刷的...
-
问 wow怎么关闭自动修理
提问时间:2024-05-07 18:22:32
答 楼主如果用的是大脚插件,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大脚标志,找一个叫售卖助手的,把修理助手勾掉,就可以直接修所有带着的装备了~祝楼主早日把插件用通~
-
问 dnf自动修理是一天只能修6次 还是一天每个角色能修6次?
提问时间:2024-05-07 03:07:44
答 同一个账号下所有角色每天可以免费自动修理6次,角色a的修理次数消耗不影响角**。当某件装备耐久度为0时系统将会修理装备并消耗一次修理次数。自动修理次数每天6点重...
-
问 为什么我的dnf的自动修理,每刷完一盘图他就会自动修理,而不是等武器没耐久了才修理?
提问时间:2024-05-07 17:52:28
答 你肯定把神圣符咒放在快捷栏里了,而且符咒能量肯定见底了,所以自动修理会认为这个也是无耐久度了,每图都会自动修理,解决方法就是把符咒放在包里就行,虽然不能享受符咒...
-
问 dnf魔王契约自动修理怎么用?
提问时间:2024-05-07 16:54:55
答 01自动修理:快捷栏里或穿戴中的装备耐久度为0时,系统会自动进行免费修理;该服务项适用于所有地下城、决斗场及街头争霸;该服务每天限用6次;有耐久度的装备才会被修...
-
问 dnf召唤师的魔杖选什么的好?每次修理装备所费的修理费来自哪里?
提问时间:2024-05-07 14:55:24
答 生物系无视武器魔攻求高智 精灵系和献祭系武器魔攻一定要高 有把高强武器更好 装备一定要高智力 刷图buff最高有炼金师做的+60智的**水 嫌太贵的话 就吃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