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约定的梦幻岛》完结,你觉得怎么样?还有第二季吗?
约定的梦幻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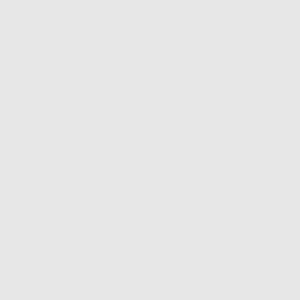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姗姗
姗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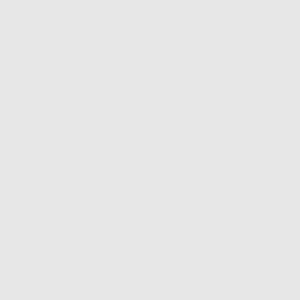 Aquarious
Aquarious
有一篇文章叫做死果。**“拉麻丹”斋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几天每个夜晚都去天台看月亮,
因为此地人告诉我,第一个满月的那一天,就是**人开斋的节日。邻居们杀羊和骆驼预备过节,我也正在等着此地妇女们用一种叫做“黑那”
的染料,将我的手掌染成土红色美丽的图案。这是此地女子们在这个节日里必然
的装饰之一。我也很喜欢入境随俗,跟她们做相同的打扮。星期六那天的周末,我们因为没有离家去大沙漠旅行的计划,所以荷西跟我
整夜都在看书。第二日我们睡到中午才起身,起床之后,又去镇上买了早班飞机送来的过期
西班牙本地的报纸。吃完了简单的中饭,我洗清了碗筷,回到客厅来。荷西埋头在享受他的报纸,我躺在地上听音乐。因为睡足了觉,我感到心情很好,计划晚上再去镇上看一场查利·卓别林的
默片—《小城之光》。当天风和日丽,空气里没有灰沙,美丽的音乐充满了小房间,是一个令人满
足而悠闲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多,沙哈拉威小孩们在窗外叫我的名字,他们要几个大口袋去装切
好的肉。我拿了一包彩色的新塑胶袋分给他们。分完了袋子,我站着望了一下沙
漠。对街正在造一批新房子,美丽沙漠的景色一天一天在被切断,我觉得十分可
惜。站了一会儿,不远处两个我认识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一辆脚踏车
丢在路边。我看,他们打得起劲,就跑上去骑他们的车子在附近转圈子玩,等到
他们打得很认真了,才停了车去劝架,不让他们再打下去。下车时,我突然看见地上有一条用麻绳串起来的本地项链,此地人男女老幼
都挂着的东西。我很自然的捡了起来,拿在手里问那两个孩子:“是你掉的东西
这两个孩子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架也不打了,一下子跳开了好几步,脸上
露出很怕的表情,异口同声的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连碰都不上来碰一
下。我觉得有点纳闷,就对孩子们说:“好,放在我门口,要是有人来找,你们
告诉他,掉的项链在门边上放着。这话说完,我就又回到屋内去听音乐。到了
四点多种,我开门去看,街上空无人迹,这条项链还是在老地方,我拿起来细细
的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小布包,一个心形的果核,还有一块铜片,这三样东西穿
在一起做成的。这种铜片我早就想要一个,后来没看见镇上有卖,小布包和果核
倒是没看过。想想这串东西那么脏,不值一块钱,说不定是别人丢掉了不要的,
我沉吟了一下,就干脆将它拾了回家来。到了家里,我很高兴的拿了给荷西看,
他说:“那么脏的东西,别人丢掉的你又去捡了。就又回到他的报纸里去了。我跑到厨房用剪刀剪断了麻绳,那个小布包嗅上去有股怪味,我不爱,就丢
到拉圾筒里去,果核也有怪味,也给丢了。只有那片像小豆腐干似的锈红色铜片
非常光滑,四周还镶了美丽的白铁皮,跟别人挂的不一样,我看了很喜欢,就用
去污粉将它洗洗干净,找了一条粗的丝带子,挂在颈子上刚好一圈,看上去很有
现代感。我又跑去找荷西,给他看,他说:“很好看,可以配黑色低胸的那件衬衫,
你挂着玩吧!我挂上了这块牌子,又去听音乐,过了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听了几卷录音带,我觉得有点瞌睡,心里感到很奇怪,才起床没几小时,怎么
会觉得全身都累呢?因为很困,我就把录音机放在胸口上平躺着,这样可以省得
起来换带子,我颈上挂的牌子就贴在录音机上。这时候,录音机没转了几下,突
然疯了一样乱转起来,音乐的速度和拍子都不对了,就好像在发怒一般。荷西跳
起来,关上了开关,奇怪的看来看去,口里喃喃自语着:“一向很好的啊,大概
是灰太多了。于是我们又趴在地上试了试,这次更糟,录音带全部缠在一起了,我们用发
夹把一卷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带子挑出来。荷西去找工具,开始要修。荷西去拿工具的时候,我就用手在打那个录音机,因为家里的电动用具坏了
时,被我乱拍乱打,它们往往就会又好起来,实在不必拆开来修。才拍了一下,我觉得鼻子痒,打了一个喷嚏。我过去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病,常常要打喷嚏,鼻子很容易发炎,但是前一
阵被一个西班牙**生给治好了,好久没有再发。这下又开始打喷嚏,我口里说着
“哈,又来了!一面站起来去拿卫生纸,因为照我的经验这一下马上会流清
鼻水。去浴室的路不过三五步,我又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同时觉得右眼有些不
舒服,照照镜子,眼角有一点点红,我也不去理它,因为鼻涕要**来了。等我连续打了快二十多个喷嚏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以往很少会这么不
断的打。我还是不很在意,去厨房翻出一粒**来吃下去,但是二十多个喷嚏打完
了,不到十秒钟,又更惊天动地的连续下去。荷西站在一旁,满脸不解的说:
**生根本没有**好嘛!我点点头,又捂着鼻子哈啾哈啾的打,连话都没法说,
狼狈得很。一共打了一百多个喷嚏,我已经眼泪鼻涕得一塌糊涂了,好不容易它
停了几分钟,我赶快跑到窗口去吸新鲜空气。荷西去厨房做了一杯热水,放了几
片茶叶给我喝下去。**在椅子上喝了几口茶,一面擦鼻涕,一面觉得眼睛那块红的地方热起来
再跑去照照镜子,它已经肿了一块,那么快,不到二十分钟,我很奇怪,但是
还是不在意,因为我得先止住我的喷嚏,它们偶尔几十秒钟还是在打。我手里抱
了一个字纸篓,一面擦鼻涕一面丢,等到下一个像台风速度也似的大喷嚏打出来
鼻血也**来了,我转身对荷西说:“不行,打出血来了啦!再一看荷西,
他在我跟前急剧的一晃。像是电影镜头放横了一样,接着四周的墙,天花板都旋
转起来。我扑上去抓住他,对他叫:“是不是**,我头晕—”
他说:“没有啊!你快躺下来。上来抱住我。我当时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被弄得莫名其妙,这短短半小时里,我到底为什
么突然变得这个样子。荷西拖了我往卧室走,我眼前天旋地转,闭上眼睛,人好似也上下倒置了一
样在晕。躺在床上没有几分钟,胃里觉得不对劲,挣扎着冲去浴室,开始大声的
呕吐起来。过去我常常会呕吐,但是不是那种吐法,那天的身体里不只是胃在翻腾,好
像全身的内脏都要呕出来似的疯狂的在折磨我,呕完了中午吃的东西,开始呕清
水,呕完了清水,吐黄色的苦胆,吐完了苦水,没有东西再吐了,我就不能控制
的大声干呕。荷西从后面用力抱住我,我就这么吐啊,打喷嚏啊,流鼻血啊,直
到我气力完完全全用尽了,坐在地上为止。他将我又拖回床上去,用毛巾替我擦脸,一面着急的问:“你吃了什么脏东
西?是不是食物中毒?我有气无力的回答他:“不泻,不是吃坏了。就闭上眼睛休息,躺了一下
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又都不见了,身体内像海浪一样奔腾的那股力量消逝了。我觉得全身虚脱,流了一身冷汗,但是房子不转了,喷嚏也不打了,胃也没有什
么不舒服,我对荷西说:“要喝茶。荷西跳起来去拿茶,我喝了一口,没几分钟人觉得完全好了,就坐起来,张
大眼睛呆呆的靠着。荷西**我的脉搏,又用力按我的肚子,问我:“痛不痛?痛不痛?我说
“不痛,好了,真奇怪。就要下床来,他看看我,真的好了,呆了一下,就
说:“你还是躺着,我去做个热水袋给你。我说:“真的好了,不用去弄。这时荷西突然扳住我的脸,对我说:“咦,你的眼睛什么时候肿得那么大了
我伸手**,右眼肿得高高的了。我说:“我去照镜子看看!下床来没走了几步路,胃突然像有人用鞭子打
了一下似的一痛,我“哦”的叫了一声,蹲了下去,这个奇怪的胃开始抽起筋来
我快步回到床上去,这个痛像闪电似的捉住了我,我觉得我的胃里有人用手在
扭它,在绞它。我缩着身体努力去对抗它,但是还是忍不住**起来,忍着忍着
这种痛不断的加重,我开始无法控制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口里尖叫出来,痛到
后来,我眼前一片黑暗,只听见自己像野兽一样在狂叫。荷西伸手过来要替我揉
胃,我用力推开他,大喊着:“不要碰我啊!我坐起来,又跌下去,痉挛性的剧痛并不停止。我叫哑了嗓子,胸口肺里面
也连着痛起来,每一吸气,肺叶尖也在抽筋。这时我好似一个破布娃娃,正在被
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东西将我一片一片在撕碎。我眼前完全是黑的。什么都看不
见,神智是很清楚的,只是身体做了剧痛的奴隶,在做没有效果的挣扎。我喊不
动了,开始咬枕头,抓床单,汗湿透了全身。荷西跪在床边,焦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不断的用中文叫我在小时候只有父
母和姐姐叫我的小名—“妹妹!妹妹!妹妹—”我听到这个声音,呆了一下
四周一片黑暗,耳朵里好似有很重的声音在**,又像雷鸣一样轰轰的打过来
剧痛却一刻也不释放我,我开始还尖叫起来,我听见自己用中文在乱叫:“姆
妈啊!爹爹啊!我要死啦!我痛啊—”
我当时没有思想任何事情,我口里在尖叫着,身上能感觉的就是在被人扭断
了内脏似的痛得发狂。荷西将我抱起来往外面走,他开了大门,将**在门上,再跑去开了车子,
把我放进去,我知道自己在外面了,就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痛。强烈的光线照进
来,我闭上眼睛,觉得怕光怕得不得了,我用手蒙住眼睛对荷西说:“光线,我
不要光,快挡住我。他没有理我,我又尖叫:“荷西,光太强了。他从后座
抓了一条毛巾丢给我,我不知怎的,怕得拿毛巾马上把自己盖起来,趴在膝盖上
星期天的沙漠**院当然不可能有**生,荷西找不到人,一言不发的掉转车头
往沙漠军团的营房开去。我们到了营房边,卫兵一看见我那个样子,连忙上来帮
忙,两个人将我半拖半抱的抬进**疗室,卫兵马上叫人去找**官。我躺在病台上
觉得人又慢慢好过来了,耳朵不响了,眼睛不黑了,胃不痛了,等到二十多分
钟之后,**官快步进来时,我已经坐起来了,只是有点虚,别的都很正常。荷西将这个下午排山倒海似的病情讲给**生听,**生给我听了心脏,把了脉
搏,又看看我的舌头,敲敲我的胃,我什么都不在痛了,只是心跳有点快。他很
奇怪的叹了口气,对荷西说:“她很好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我看荷西很泄气,好似骗了**官一场似的不好意思,他说:“你看看她的眼
睛。**官扳过我的眼睛来看看,说:“灌脓了,发炎好多天了吧?我们拼命
否认,说是一小时之内肿起来的。**官看了一下,给我打了一针消炎针,他再看
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是在跟他开玩笑,于是说:“也许是食物中毒。我说:
不是,我没有泻肚子。他又说:“也许是过敏,吃错了东西。我又说:“皮
肤上没有红斑,不是食物过敏。**官很耐性的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你
躺下来,如果再吐了再剧痛了马上来叫我。说完他走掉了。说也奇怪,我前一
小时好似厉鬼附身一样的病痛,在诊疗室里完完全全没有再发。半小时过去了,
卫兵和荷西将我扶上车,卫兵很和善的说:“要再发了马上回来。坐在车上我觉得很累,荷西对我说:“你趴在我身上。我就趴在他肩上闭
着眼睛,颈上的牌子斜斜的垂在他腿上。沙漠军团往回家的路上,是一条很斜的下坡道。荷西发动了车子,慢慢的滑
下去,滑了不到几公尺,我感到车子意外的轻,荷西并没有踏油门,但是车子好
像有人在后面推似的加快滑下去。荷西用力踏煞车,煞车不灵了,我看见他马上
拉手煞车,将排档换到一档,同时紧张的对我说:“三毛,抱紧我!车子失速
的开始往下坡飞似的冲下去,他又去踩煞车,但是煞车硬硬的卡住了,斜坡并不
是很高的,照理说车子再滑也不可能那么快,一刹间我们好像浮起来似的往下滑
下去,荷西又大声叫我:“抓紧我,不要怕。我张大了眼睛,看见荷西前面的
路飞也似的扑上来,我要叫,喉咙像被卡住了似的叫不出来。正对面来了一辆十
**卡车的**,我们眼看就要撞上去了,我这才“啊—”一下的狂叫出来,
荷西用力一扭方向盘,我们的车子冲出路边,又滑了好久不停,荷西看见前面有
一个沙堆,他拿车子一下往沙里撞去,车停住了,我们两个人在灰天灰地的沙堆
里吓得手脚冰冷,瘫了下来。对面那辆**上的人马上下来了,他们往我们跑来
一面问:“没事吧?还好吧!我们只会点头,话也不会回答。等他们拿了铲子来除沙时,我们还软在位子上,好像给人催眠过了似的。荷
西过了好一会,才说出一个字来,他对那些军人说:“是煞车。驾驶兵叫荷西
下车,他来试试车。就有那么吓人,车子发动了之后,他一次一次的试煞车都是 ...
-
问 对于《延禧攻略》的大结局,你觉得怎么样?
提问时间:2024-04-20 14:20:34
答 昨天看了大结局,陪伴了一个假期的大剧也终于结束,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悲伤。先说傅璎;当听到海兰察带回傅恒临死前的话时,瞬间泪崩了,尤其是璎珞差走了身边人后,说,'好...
-
问 你们觉得腾讯的龙族幻想怎么样?
提问时间:2024-04-20 04:32:07
答 {!pgc_video:{"thumb_height":642,"file_sign":"8c98c54c4cbbfa82688a8307112d6ac3","...
-
问 梦幻西游!副本前世今生2的第二环,怎样完成??
提问时间:2024-04-20 19:21:37
答 第二环,请仙密阵 限时90分流程:(3个队伍时一般20分钟内可完成本环)方寸觉明处进入副本场景,场景内有12木头机关人,每个木头人有各自的名字。进场后队长找中间...
-
问 你觉得《伪恋》的结局怎么样?
提问时间:2024-04-20 06:23:54
答 不知道你问的是动画还是漫画?如果是动画的话,这道题我刚好能答,最近也是是花了点时间补完了这部久仰大名的动漫,要说观看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毕竟原作是在jump上面连...
-
问 美恐第二季 结局是什么
提问时间:2024-04-20 23:55:12
答 结局:裘德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沃克来到床边与裘德决别,裘德临死之前看到了黑衣天使,黑衣天使来到床边亲吻裘德。记者们采访完拉娜告辞离去,约翰尼来到拉娜身边坐下,拉...
-
问 《文豪野犬》第三季完结了吗,结局说了什么?
提问时间:2024-04-20 04:25:27
答 《文豪野犬》在近日已经更新到第12话,第三季主要就是围绕着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搞事而展开,本话就是**侦探社、港口**与死屋之鼠的最终决战,结果在太宰治的掌...
-
问 你们觉得《第五人格》里的环境怎么样?
提问时间:2024-04-20 03:38:27
答 谢谢邀请我个人觉得,军工厂很容易溜屠夫,毕竟大家接触的第一个地图,应该就是军工厂了吧,我对着一个地图,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个人思想)第二个是红教堂,想必大家都不...
-
问 你了解**吗?你觉得怎么样?
提问时间:2024-04-20 15:13:41
答 **,地理位置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的西北,内陆的内陆,面积160万平方公里,东西走向的天山山脉把**分隔为南疆和北疆,北疆天山和阿尔泰山脉之间为准葛尔盆地和古...